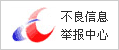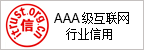引言:史家笔下的禅门心灯
钱穆先生(1895-1990)以儒学与史学名世,其《国史大纲》、《先秦诸子系年》等著作巍然如山,被誉为“最后一位国学大师”。然而,在这位以梳理中华文化血脉为己任的儒者心中,禅宗却占据着一方独特而明亮的天地。他非佛门信徒,却对禅宗投以深切的“温情与敬意”;他是儒家价值观的捍卫者,却斩钉截铁地断言,不理解禅宗,便不能理解宋明理学,乃至唐宋以后中国文化的全体风貌。这不仅是一种学术判断,更是一种宏阔的文化史观。今日,就让我们跟随宾四先生的目光,拨开历史的迷雾,看他如何以史家之如椽大笔,点亮那盏照亮中国思想交汇之路的禅门心灯。
第一章 通儒与达禅:钱穆的学术人生与禅缘
钱穆,字宾四,江苏无锡七房桥人。他的人生,是一部自学成才的旷世传奇。从无锡乡间的中学教师,到北京大学的讲坛巨星,再到于香港赤手空拳创办新亚书院,其一生颠沛流离,却始终守护着中国文化的火种。他仅有中学学历,却凭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之精微考据一鸣惊人,以《国史大纲》之宏大叙事震撼学林,奠定了其在中国史学界无可撼动的宗师地位。他的学术根底深植于儒家,但其视野却贯通经史子集,包罗万象,对中华文明的一切创造皆抱有“了解之同情”。
而他与禅宗的深缘,则始于1915年执教小学时对《六祖坛经》的初次阅读。真正的豁然开朗,则是在1944年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,他避居于四川灌县灵岩山寺。青灯古佛之下,他暂时远离战乱,系统阅读了《指月录》等禅宗典籍。此番沉浸,他自谓“如桶底脱”,以往积郁的学术困惑顿时豁然。正是这段经历,让他真切地认识到,禅宗绝非简单的“出世”或“空寂”之学,而是一种深刻的心性智慧与活泼泼的生命哲学,其精神内核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紧密相连。
第二章 入世与超然:钱穆对禅宗的基本态度
钱穆作为儒家学者,其思想核心无疑是“入世”与“经世致用”。但他对禅宗的态度,并非简单的排斥或否定,而是一种基于历史洞察的深刻理解与批判性吸收,展现出一种难得的 intellectual generosity(智识上的慷慨)。
核心观点一: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巅峰之作
在《国史大纲》这部不朽之作中,他明确地指出:“禅宗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代表,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(尤其是道家、玄学)融合的产物,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创造性。” 他认为,禅宗的兴起与成功,是外来文化被中华文明成功消化、吸收并创造性转化的最佳范例。它不再是印度的佛教,而是地地道道的“中国禅”,其精神气质已深深打上了华夏民族的烙印。
核心观点二:肯定禅宗的社会与文化影响
他多次在其著作中强调,“在《国史大纲》《中国思想史》等著作中,他肯定禅宗对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影响。” 他认为,禅宗的一大功绩在于将高深玄妙的佛理平民化、生活化,使其精神如春雨般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,从士大夫的修身养性、艺术创作,到平民百姓的处世哲学、人伦日用,无不有其深刻烙印。
第三章 革命与奠基:钱穆论慧能与《坛经》
在钱穆看来,慧能及其《坛经》在中国思想史上完成了一场“寂静的革命”,其声势不显于外,其力量却震撼于心。
1. 《坛经》的崇高地位:“中国人的佛经”
钱穆给予《坛经》以无与伦比的评价。他不仅大胆地将其列入中国人必读的“新七经”之一,更着力强调其独特性与革命性:“在全部佛教典籍中,《坛经》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(慧能)讲述而被尊为‘经’的著作。这本身就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,它不再是印度思想的翻版,而是独创性的中国智慧。” 这一论断,从文化主权的高度,确立了《坛经》的划时代意义。
2. 慧能的革命性:“不识字的圣人”
钱穆盛赞慧能的“顿悟”学说,认为它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,其功绩可归结为三点:
①消解繁琐:他幽默而精辟地比喻道:“印度佛学像进口咖啡,慧能把它调成了中国茶。” 他认为,针对唐代佛教日益繁琐的经院哲学与累世修行的桎梏,慧能高扬“不立文字,直指人心”的大旗,如同一次成功的“佛学减肥”,让修行从“读万卷经”的沉重负担,回归到“明一念心”的内在觉醒。
②自性觉醒:钱穆特别欣赏“运水搬柴,无非妙道”的思想,认为这石破天惊之语,一举将佛法从森严的寺院拉回了鲜活的厨房与市井,堪称“人间佛教”的先声。他将慧能的核心思想精辟地总结为“自性本自具足”六个字,认为这彻底将成佛的根据从外在的经典、仪式和偶像,内化为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、圆满无缺的“自性”。
③真修实悟:钱穆坚决反对后世将“顿悟”理解为不劳而获的灵光一闪。他以慧能在五祖门下“踏碓八月”、得法后“南奔潜行”十五年的经历强调:“无真修岂有真悟?” 并调侃道:“若以为顿悟是闪电速成班,那慧能该是千古第一‘作弊生’了。” 这表明,在钱穆看来,顿悟是长期笃实修行后瓜熟蒂落的必然结果。
3. 对宋明理学的奠基作用
钱穆深刻地指出,隋唐佛学(尤其是禅宗)的巨大贡献,在于将中国思想界的焦点从宇宙论(如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)转向了心性论。慧能对“本心”、“自性”的深入探讨与极致张扬,为后来的宋儒研究“心”、“性”、“理”等核心范畴,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思想资源和迫切的问题意识。因此,他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:“不了解慧能与《坛经》,就无法理解宋明理学的兴起。”
第四章 吸收与划界:钱穆析朱熹与禅宗的关系
这是钱穆禅学研究中最具创见、也最为精彩的华章。他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,清晰地揭示了宋明理学与禅宗之间“批判中吸收,超越中融合”的复杂辩证关系。
1. 朱子与禅的“爱恨情仇”
钱穆洞察到,朱熹早年曾深入浸淫于禅学,其思想根基深受熏陶,后来虽在立场上“逃禅归儒”,但其思维深处始终带有禅宗的深刻烙印。对此,他有一个极为精妙的比喻:
“朱子辟禅,正因懂禅太深——如同美食家才知如何批判菜谱。”“朱子从禅宗‘借’来兵器,却用来守卫儒家城池。”
这两句话,将朱熹与禅宗那种剪不断、理还乱的复杂关系,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2. 儒禅之争的三大焦点(根本立场的对立)
钱穆着力辨析了二者在根本立场上的巨大差异,这正是朱熹对禅宗批判的核心所在。
(1)宇宙论与人生论的根基不同:
禅宗:认为“万法唯心”,一切外在世界(山河大地)皆是心识所变,本质是“空”。因此,其终极追求是出离世间,证悟此心本空。
朱熹:认为“性即理”。宇宙间有一个客观、实在的“天理”,它既存在于人心(为性),也充盈于万物。人生的目的不是出离,而是在人伦日用(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)中格物穷理,通过认识万物之理来印证内心之性,最终达到“与理为一”的境界。
钱穆的比喻:禅宗是“空房子”,理学是“精装修”。一个要拆解一切固有结构,回归空性;一个要在此结构内精心布置,安顿人生与社会。
(2)对“心”的理解不同:
禅宗:追求心的“空寂”、“无滞无碍”,要切断一切执著,包括对善恶、是非的分别心。
朱熹:认为心是“知觉”和“主宰”,其核心功能是认知“理”并践行道德(如仁、义、礼、智)。心不是要空掉,而是要装满“天理”,并以此理来应事接物,做出价值判断。
(3)对社会人伦的态度不同(最根本的差异):
禅宗:以其“出世”的本质,消解了世俗伦理的终极意义。虽然也讲“佛法在世间,不离世间觉”,但其最终目的是超越世间,其伦理是“方便法门”。
朱熹:儒家则以构建和维护世俗人伦秩序为最高使命。他的全部学问,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,最终都要落在“修齐治平”这八个字上。这是与禅宗根本对立的入世精神。
钱穆的精辟总结:他指出,朱熹对禅宗的批判,并非简单的门户之见,而是原则性的、根本立场的划界。他用八个字概括这种关系:“目的同而归趣殊”。意思是,双方都致力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(目的同),但最终的指向和落脚点完全不同(归趣殊)。朱熹正是吸收了禅宗在心性修养上的精密工夫,却将其方向盘完全扭转,重新锚定在儒家的现实关怀与社会责任之上。可以说,朱熹是“用禅宗的枪,打儒家的靶”,完成了对禅宗的创造性转化。
第五章 辨章学术:钱穆禅学观与近当代学者的对话
钱穆先生的禅学研究绝非闭门造车,而是始终处于与同时代顶尖学者的思想激荡与对话网络之中。深入这些或显或隐的学术交锋,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其禅学观的独特定位与价值。
1. 与陈寅恪:心史与制度史的呼应陈寅恪先生更侧重于从“制度史”与“社会史”的精密视角考察佛教,如佛教与中古政治格局、社会经济(如寺院庄园、僧尼免赋役)的复杂关系。而钱穆则侧重于“思想史”与“心史”,更关注禅宗如何回应时代的核心问题,并安顿中国人的内心世界。二者一重外在脉络,一重内在理路,恰成奇妙的互补。钱穆曾言:
“研究思想史,不能只看思想家说什么,更要看他的时代需要什么,他的心灵在追寻什么。”这种对“心灵追寻”的侧重,正是其“心史”的体现,与陈寅恪先生客观冷静的制度史研究,共同构成了隋唐佛教研究的双璧,相映成趣。
2. 与汤用彤:思想脉络的两种梳理汤用彤先生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以精密的考据和深邃的哲学分析见长,重在梳理佛教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、概念嬗变与义理发展。而钱穆则更善于将禅宗置于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脉络中,揭示其与儒家、道家思想的互动、碰撞与最终融合。简而言之,汤公重在其“本身的精微”,钱公重在其“关系的广大”。前者是佛学研究的深度掘进,后者是文化史观的宏大叙事。
3. 与吕澂:佛学本源之辩吕澂先生作为学养深厚的佛学大家,精通梵、藏文献,强调必须从印度佛学本源来审视中国佛教的“失真”与“歧变”。而钱穆则恰恰从文化史的立场出发,认为这种所谓的“歧变”正是成功的“转化”与“创造”,是中国文化强大主体性与消化能力的彰显。这一根本性的分歧,生动地体现了“佛学内部的本位视角”与“文化史家的外部视角”在学术路径上的根本差异。
第六章 门风各异:钱穆论禅宗五家之旨趣
钱穆先生对禅宗的研究并未止于慧能,他对慧能之后“一花开五叶”所形成的不同宗派,其各自鲜明的宗风与接引学人的手段,亦有精到的观察与比较。
1. 临济宗:钱穆评其宗风在“机锋峻烈”,如“当头棒喝”,旨在以极其迅猛激烈的手段,截断学人的思维葛藤,令其于言语道断、心行处灭的瞬息间豁然醒悟。他认为此法“气势磅礴,如大将军之令,不容拟议”,最易接引上根利器,但也最易流于粗狂,若学人根器不足,则如“蚊子叮铁牛”,无下嘴处。
2. 曹洞宗:钱穆指出其宗风在“默照暗推”,如“农夫耘田,绵绵密密”。他在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中提及,曹洞宗风“绵密回互,言行相应”,提倡于长期的静坐默照中休歇妄心,默默体证本性,其风格更近于儒者的“主敬”与“慎独”功夫,于平凡踏实中见真章。
3. 云门宗:钱穆欣赏其宗风高古,如“云门三句”(函盖乾坤、截断众流、随波逐浪)气势恢宏,涵盖宇宙。他认为云门宗“孤危险峻”,语句简洁而意境高远,需有极深的文化涵养与悟性方能领会,是禅宗精神与士大夫文化深度结合的典范。
4. 法眼宗与沩仰宗:钱穆亦有点评,他指出法眼宗重“对病施药,相身裁缝”,强调应机接物,灵活善巧,其风较为平实。而沩仰宗则规模严谨,师资唱和,父子一家,门风温和圆融,有如古之田园礼乐。
钱穆的总评尤为精彩,他宏观地概括道:
“临济如天马行空,曹洞如老农耘田,云门如天子登殿,法眼如郎中开方,沩仰如家族唱和。五家宗风,实为中国文化性格在禅门中之五种表现。”此论高屋建瓴,将禅宗各派的精神气质与中国文化内在的多样性、丰富性联系起来,见解极为深刻,体现了其通儒的宏阔视野。
第七章 反思、考据与融合
1. 对“不立文字”的深刻反思作为一位极其重视经典传承与历史文献的学者,钱穆对禅宗“不立文字、教外别传”的传统抱有深刻的警惕与反思。他认为,其长处在于能打破桎梏,直探心源,但流弊亦随之而来:
“过度强调‘离言说相’可能导致虚玄空疏,甚至落入‘狂禅’的弊病;儒家则更注重‘以文载道’,通过经典传承与学术积累维系文化的延续性。”他进一步阐述,如果完全摒弃文字和经典,容易使思想失去标准和依归,流于空疏和狂妄,所谓“暗证生盲”,学者无绳墨可循。相比之下,儒家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”的传统,更能保障文化的稳健传承与有序发展。
2. 考据与求真:与胡适的《坛经》公案钱穆不仅从思想层面研究禅宗,更从历史考据入手,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与胡适关于《坛经》作者的学术公案。
胡适观点:主要依据敦煌发现的《神会语录》等文献,断言《坛经》是神会或其门徒为争法统而伪作。
钱穆反驳:他连续发表《神会与坛经》等系列论文,从多个角度进行辩驳:
他指出,韦处厚为慧能弟子神会所作碑文中的“《坛经》传宗”实为禅门“嗣法”之意,并非指伪作。 他认为,慧能预言之说“虽怪诞未必神会自炫”,更可能是后世弟子在传播中的附会增饰。 他始终坚持“慧能到底是南宗开山,神会不过是《坛经》传宗”的基本判断。
方法论的交锋:
钱穆在方法论上批评胡适仅依孤立的敦煌文献立论是“如盲人摸象”,只见局部而未见全体。他自己则致力于结合传统史传、文人文集、禅门语录等多种史料,力图重构禅宗历史的整体图景与演变脉络。这场辩论,不仅关乎一桩历史公案,更展现了史学家不同的史料观与历史想象力。
3. 禅宗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在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等作品中,钱穆以其宏阔的文化史观指出:
“禅宗的兴盛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思想的消化能力。禅宗将佛教的‘解脱’转化为生活中的‘平常心是道’,与中国农耕文明中注重现实、强调人伦日用的特质相结合,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。”
他强调,禅宗的成功融入,正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包容性、同化力和顽强主体性的明证。它既深刻地改变了佛教的面貌,也被中国文化的土壤所改变,最终成就了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的文化盛景与思想共业。
第八章 原典的光芒:钱穆论禅著述精选
本章将集中呈现钱穆先生著作中的相关原文,让我们直面其思想的第一现场,感受其文字的力量与见解的深度。
1. 论禅宗的历史地位与革命性
“禅宗崛起,实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革命。其最要宗旨,在‘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’。自达摩东来,直至慧能,而此一大革命始告完成。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之影响,至深且巨。”——《中国思想史》,联经出版公司,第199页“唐代之禅宗,实是佛教之简化与南方化。亦可说是佛教之中国化。……他们把人的地位提高了,把人的责任加重了。……这是中国思想史里一番大革命。”——《中国史学发微》,东大图书公司,第85页
2. 论《坛经》的价值与慧能的贡献
“《六祖坛经》,正是中国佛学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著而尊称为‘经’的书籍。……我们可以说,慧能是中国佛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。他把印度传来的佛教,彻底转化为中国佛教。”——《六祖坛经大义》,载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四),三联书店,第123页“慧能讲佛法,只是‘本来无一物’,只是‘自性自度’。……一切外在的修行,一切经典的研寻,到此全无用处。这是佛学上一番最彻底的大解放。”——《中国思想史》,第205页
3. 论朱熹与禅宗的复杂关系
“朱子虽力辟禅学,然其自己修养方法,则实有资于禅者。如主敬、静坐,皆与禅定相近。……其分别处,则禅家要出世,儒家要入世。此为儒释疆界所判。”——《朱子新学案》,九州出版社,第贰册,第312页“理学家所争,在禅宗主张‘无善无恶’,而理学家则必要讲‘性善’。……禅宗是‘作用见性’,理学家则必要说‘性即理’。此是儒释疆界一大分辨。”——《中国思想史》,第231页
4. 论“不立文字”的利弊与文化融合
“禅宗主张‘不立文字’,‘教外别传’。其长处,在能摆脱拘挛,直探心源。其流弊,则易陷于空疏狂妄,甚至‘野狐禅’,‘口头禅’,尽失佛教本来精神。”——《中国学术通义》,台湾学生书局,第177页“中国文化之伟大处,正在其能容纳外来思想,而终能加以消化,使之转变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。如禅宗,虽源出印度,然经中国人一番消化,遂成为一种最富中国气息之佛教。”——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,商务印书馆,第165页
第九章 余响:钱穆禅学观的传承与影响
钱穆先生的禅学研究,如同投入思想湖面的一颗巨石,其涟漪远播,对其弟子及后世学界产生了深远而细致的影响。
1. 对余英时先生的影响其高足、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,完全继承了其师将思想置于广阔历史脉络中考察的“史家立场”。他在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》等典范性著作中,进一步精密地论证了禅宗(尤其是新禅宗)的“入世苦行”精神,如何为宋明新儒家的伦理观,乃至明清商人的精神气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内在动力。这可以看作是对钱穆“禅宗启理学”这一核心观点的精密化、具体化与卓越的深化。
2. 与新儒家的对话另一位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,则从哲学体系建构的角度,对禅宗有更严格的判教。他认为禅宗是“只有作用层,而无存有层”,即只在“破执”的消极层面有功,但未能积极地为道德价值建立形而上的超越基础(存有层)。这一深刻而严厉的批判性讨论,正好从反面印证并丰富了钱穆的观点——宋明理学正是吸收了禅宗精深的心性工夫(作用层),而后为其坚实补上了“存有层”(天理)的形而上学根基,从而完成了对禅宗的创造性超越。钱、牟二人,一从历史入,一从哲学出,共同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。
结语:在史实与义理之间
钱穆先生曾自陈心迹:“读禅非为逃世,乃为更好地入世。” 这句话,道出了他作为儒者研究禅宗的最终目的——绝非为了逃避现实,而是为了汲取异质文化的智慧,以期更积极、更从容、更智慧地面对人生和世界。他笔下的禅宗,是活泼泼的、入世的、充满中国智慧的生命哲学。
通过他的解读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“佛教中国化”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,更是一位深具文化使命感的儒者,在古今交汇、中西碰撞的激荡时代里,为安顿民族心灵、延续文化血脉所做的艰苦而卓越的努力。
这份跨越时空的智慧,这份对自身文化“温情与敬意”的坚守,至今仍在为我们指引方向,提醒着我们:“文化如人,积存与消化缺一不可。”
(刘东亮于2025.11.17于上蔡古国鸳鸯镇